

文字整理 | 中霖
【目录】
第五篇 为义而活,为仁可过
第六篇 内守敬,外行简,是谓德行
第七篇 立大本,才能传道统
第八篇 天下是让出来的,而不是争出来的
【正文】
第五篇 为义而活,为仁可过
◎子谓公冶长:“可妻也,虽在缧绁之中,非其罪也。”以其子妻之。
这一章的关键句是:非其罪也。
这一章孔子评论他的女婿公冶长,从“可妻也”到“以其子妻之”,这是非常具体的表扬,而且真正付出实际的行动,可见对于公冶长的评价十分肯定。让读者比较纳闷的是:第一点,公冶长坐过牢;第二点,没有具体说明公冶长犯了什么罪;第三点,只留下“非其罪也”这个谜团给大家。尤其是“非其罪也”这一句,值得我们好好发想。
选女婿这件大事,我们可以理解孔子心中自有一把尺,他要的是有良知、有正义、有行动力、有理想性的真男子,“罪不罪”这种有形的论断,孔子有他的辨识标准。孔子处在那个动荡的时代,政治不清明,或者贪墨横行,或者君王失道……孔子恐怕有相当的考虑。所以,“非其罪也”,这是个好话题,值得我们探讨与思考。
下一章孔子也帮他的侄女儿安排了婚事,整章重要的关键是“邦无道,免于刑戮”,和选女婿的着眼点并不相同,从这个角度看去,孔子因人制宜、因事制宜,他有他权宜的考虑。选女婿可以照自己的理想,孔子可以负全责,他客观、冷静,还带有一点理想性。可是选侄女婿,这是帮别人决定婚姻大事,孔子反而采取保守的立场,在婚姻的生活面、幸福面、安全面,考虑比较周全。这一点值得我们深思,面对实际的人生,人人都要有守经通权的智慧。【评:面对孩子的上学、就业等重要课题的选择,也可参考孔子的态度。自己的孩子可以走与众不同的道路,但为别人家做建议,还要随顺常情,不要过激。】
公冶长虽然定了罪也锒铛入狱,但是孔子说“非其罪也”。在孔子的心目中,“缧绁”不一定代表真理,只是有个“名目”,有个“标准”搁在那里,真正的“不仁”“不忠”“不孝”“不义”,才代表真理的审判。孔子找能见义勇为、有冒险精神的人来当女婿。这里有几个问题可以思考:
第一,公冶长人品很好:孔子说公冶长这个人,可比把女儿嫁给他为妻,证明在孔子的眼中,他的人品是不错的。不能说公冶长受了冤狱,孔子就轻易把女儿嫁给他。
第二,公冶长为义而活:好打抱不平,见义勇为,不考虑自己的存亡,孔子看他有出息。
第三,狱政不明,邦国无道:公冶长是蒙冤受罪,知子莫若父,知徒莫若师。公冶长的牢狱之灾,孔子心知肚明。
孔子把女儿嫁给自己的门生弟子公冶长,不会只是“虽在缧绁之中,非其罪也”,这么轻描淡写的理由;或者狱政不明,受了一场冤狱,然后就“以其子妻之”。从《论语》一书来解读,公冶长之所以能够成为孔家的乘龙快婿,公冶长“为仁而过”或“为义而罪”是“虽在缧绁之中,非其罪也,以其子妻之”比较合理的理由。我们先说“为仁而过”:
在《论语·里仁第四07》子曰:“人之过也,各于其党。观过,斯知仁矣。”我们已经有详细的阐释,现在我们把焦点放在——“观过,斯知仁矣”,这是孔子从“过”来谈“仁”的问题,这个思考或角度都是很特别的。“人之过也,各于其党”。哪一类的人,犯哪一类的过,这是很简单就可以推论的。可是孔子他把过错这件事,集中焦点来讨论仁,这是很特别的。
为什么要说观察一个人所犯的过错,就可以知道他仁或不仁?【评:其实,透过现象看本质,人人都有这个天赋的能力,因为良知本具。】关键在讨论,是“为仁而过”或者“为不仁而过”对不对?同样的,孔子品评公冶长,显然有很高的评价,“虽在缧绁之中,非其罪也”,“罪不罪”不是孔子要作为考虑嫁女儿、选女婿的关键点,公冶长应该有让孔子折服之处,这才是合理的。
从历史的眼光来看,有人“为仁而过”,正因为这种“为仁而过”才现出他的仁心仁德,才万古流芳。所以,仁人志士真想有一点成就,一定要有强大而坚定的精神力量,才能“我欲仁,斯仁至矣”,才能“造次必于是,颠沛必于是”,老祖宗给的就是“仁义”。可以为仁义而“过”,不能为仁义而“恶”。为仁义而恶是“似是而非”的诡论,因为,因源于不仁义的“恶心”是有心之失;源于仁义的“过心”是无心之过,甚至是一种超越。【评:为仁而过,甘愿遭受世人的非议,也是一种义勇。这才不是伪君子、假仁义。】
《论语·为政第二24》子曰:“见义不为,无勇也。”所以,见义勇为就成为壮士、义士的鲜明形象,荆轲刺秦王,家喻户晓。荆轲将为燕太子丹往刺秦王,燕太子丹在易水边为他饯行。高渐离击筑,荆轲和而歌曰:“风萧萧兮易水寒,壮士一去兮不复还!”然后头也不回,扬长而去,后人称为《易水歌》。荆轲的价值不在不怕死,而是为义而赴汤蹈火,抱着必死无还的心,这是荆轲为义而亡的升华。所以,有人“为义而亡”,正因为有人能“见义勇为”而舍生取义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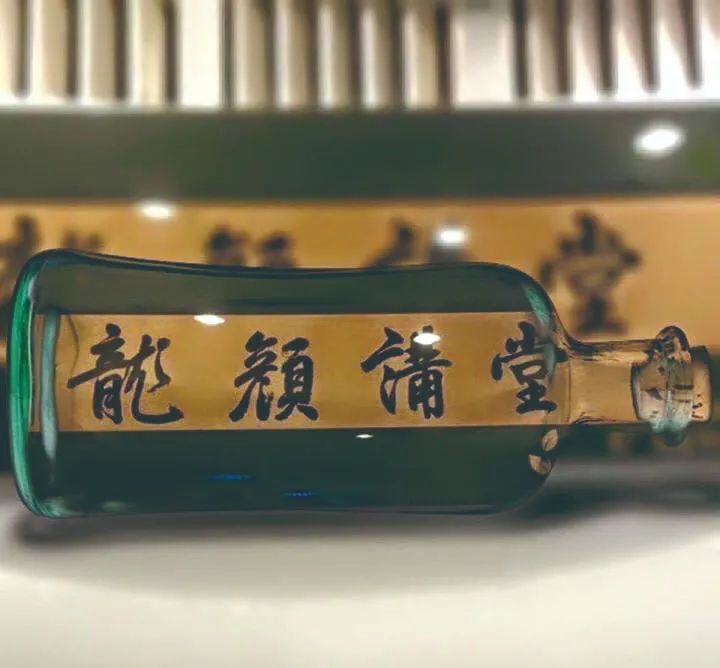
第六篇 内守敬,外行简,是谓德行
◎子曰:“雍也,可使南面。”仲弓问子桑伯子。子曰:“可也,简。”仲弓曰:“居敬而行简,以临其民,不亦可乎?居简而行简,无乃大简乎?”子曰:“雍之言然。”
为政贵简不贵繁。这一章的关键字是:敬、简。
“雍”就是冉雍,字仲弓,孔门四科十哲之一。《论语·先进第十一03》德行:颜渊、闵子骞、冉伯牛、仲弓。言语:宰我、子贡。政事:冉有、季路。文学:子游、子夏。这一章孔子赞美他“可使南面”;《论语·雍也第六05》孔子评论仲弓,以譬喻的手法,说他“骍且角”,肯定他的道德人品。
这一篇的“雍也,可使南面”,一直有几种不同的解释,值得我们来探究。孔子先说“雍也,可使南面”;冉仲弓接着以道家人物“子桑伯子”请孔子评论,从上下文看,应该是问孔子:“子桑伯子,可使南面?”孔子的回答是:“可也,简。”因为话题都是“以临其民”。所以,合为一章比较合理。
由于孔子回答仲弓,只说了一个字:“简”。所以,开启了仲弓的阐论。“居敬而行简”和“居简而行简”,仲弓在这一章中,隐隐约约引出了儒家和道家之间的比较,当然,仲弓是站在儒家的思维与立场来阐述的。听了冉仲弓的一番议论之后,最后孔子说“雍之言然”,对弟子的说法是肯定的。
以孔子的立场而言,他认为冉仲弓有君人之德。言外之意,谁有天子之德,谁就能任事。《孟子·告子下篇》“人皆可为尧舜”;《孟子·滕文公上篇》“舜何?人也;予何,人也。有为者亦若是。”《孟子》这两章,就是明证。儒家最可敬的思想就是人人都可以当天子,等到《春秋》和《易经》的境界又不同了,西汉·董仲舒《春秋繁露·俞序篇》“天下之人,人皆有士君子之行。”《易经·乾卦·文言传》“(乾卦)用九:见群龙无首,吉。”人人都是士君子、人人的才德都成龙成凤,那就接近天下太平的境界了。【评:群龙无首,呈现群性之美,这并不难做到。只要给大家充分的尊重和肯定,不是各行其是,自由主义,一片散沙,而是率众以正,就可以呈现天火同人之象。】
在刘向《说苑》一书中,记载孔子和子桑伯子曾经见面,而且是孔子求见子桑伯子,结论是孔子认为道家的子桑伯子太过随性,应该受礼法熏化;子桑伯子则认为,儒家太繁文缛节,应该要去繁就简。冉仲弓刻意锁定子桑伯子这个对象,引起话题,孔子则从道家“以简为贵”搭腔,师生一问一答,你来我往,其实所讨论的,都在治平天下这个大架构上。道家主张“无为而治”,“贵简”不“贵繁”;儒家主张“以礼治国”,“贵礼”不“贵法”。【评:大礼与天地同节,礼者,天理也;而天地之道,即至简之道。故在根本处,儒道两家是相通的。】
孔子说“可也,简”,一个“简”字,就已经高度概括道家的政治作为,也涵盖了无为而治的原理原则,十分传神。至于“可也”,是客观的认可,属于还可以的评述。“简”,是简要不繁之意。孔子认为子桑伯子的形象,富有道家的典型,所以回答仲弓之问说:“可也,简。
先秦的政治思想,其实都是“务为治”的,都希望对于“周文疲弊”的乱世提供药方子,为大时代找出一条生路。老子无为、儒家仁爱、墨家兼爱,都有可贵的思想价值。《道德经》第三章:“圣人之治,虚其心,实其腹,弱其智,强其骨,常使民无知无欲,使夫智者不敢为也,为无为,则无不治。”就政治思想而言,道家主张清静无为,这个“无为而治”的可贵处,正在发挥它的“无不为”。
道家讲无为而治,是顺自然而无为,子桑伯子是道家之徒,秉要执本,以简御繁,这是道家人君南面的政术;不干预、不扰民,它的作用则有“无不为”的妙处。儒家也讲无为而治,主张为政者恭己主敬,具体做法是分层负责。《论语·卫灵公第十五05》子曰:“无为而治者,其舜也与?恭己正南面而已矣。”先说“正南面”,重点在“正”,就是修内圣而为典型,《诗经·大雅·思齐篇》“刑(型)于寡妻,至于兄弟,以御(音讶,治也)于家邦。”这种从做“家的典范”到做“邦国的典范”,正是内圣的“正”,也就是南面的“正”。其次是“恭己”,就是“敬”的态度,“恭”与“敬”都是审慎的意思;若细分别之,“恭”对自己而言,“敬”对别人来说。【评:今天的孩子普遍缺乏恭敬心,是因为社会普遍精神坍塌。故从家家户户设明堂,立五尊开始,培养成人的恭敬心,上行下效,孩子就可以学成人的样子。】
仲弓说:“居敬而行简,以临其民,不亦可乎?”是以儒家的观点来扩大解释这个“简”,以来敦临天下之民。“无为而治”是简,强调顺自然;“正南面”也是简,着重止于至善的为天下人的典型。仲弓将“简”定调在实践的功夫,所以说,“行简”。那“居敬”呢?这个“居”同于《孟子·滕文公下篇》“居天下之广居,立天下之正位,行天下之大道”的“居”。毓老师说,“居”就是“守”的意思(居天下之广居:守住天下人民广大居住之地)。“居敬”就是“守敬”,恭己不就是守敬吗?以敬守自己的心(本心),以敬守自己之身(行为),这就是儒家的守敬功夫,是内圣的入手处。【评:孔子指出的内修之路,平易可行,不需要跑到山洞里闭关,也不必皈依什么上师,就从日常的待人处事做起。】仲弓的“居敬而行简,以临其民”,把儒家的“内圣外王”之道,说得非常透彻!临民之道,就在施惠,贵精不贵多、贵简不贵繁,施惠是讲具体的“因民之所利而利之”,政治是实惠的,要把复杂的简单化。所以,“行简”,明明白白去做对的事,不用拐弯抹角,也不用矫情干誉。
《论语·学而第一05》子曰:“道(导)千乘之国,敬事而信,节用而爱人,使民以时。”居敬不是只有戒慎恐惧的态度而已,还要真正把事做好,这才是完全而完美的“居敬”。孔子说“敬事而信”,能履行诚信就是完全落实“敬事”而有成。【评:阳明讲的“在事上磨”,就是“致良知”的具体举措。而落实到“致礼乐”,就是尊老爱幼,老者安之,朋友信之,少者怀之。】
“道(导)千乘之国”“道(导)万乘之天下”莫非此理。这才是在“礼义”之下,真正能发挥作用的“敬德”,德不是用讲的,德行都是善行的具体结果。毓老师特别借北宋·周濂溪《太极图说》的“主静立人极”,套入说成“居敬立人极”。必须“守敬”才能达到“人极”,如何达到人中之极的境界呢?中国人是从“太极”发想的,太极是生命之元的伊始,这个生命哲学的源头,虽然无法印证,却元亨利贞,透过阴阳合德而造生万物,使万有生生不息,这是元德,故曰元首。
“人者,天地之心也”,学元德、学天德、学地德,学大自然之德。所以,元心、天心(地心)、仁心,三心,一也。学“生”之“太极”,学“生”之“元首”,无私无我,大化万有;在人的世界中,仁德臻乎人极的圣人,就必须是全方位的大人,与天地合、与日月合、与四时合、与鬼神合。“立人极”就得从“守敬”开始,儒家以礼义教人,《礼记》的第一句话就点出“毋不敬”是安民的基础,《礼记·曲礼上篇》“曲礼曰:毋不敬,俨若思,安定辞。安民哉!”这和这一章“居敬而行简,以临其民,不亦可乎?”不是隐隐相呼应吗?
在为政的概念上,仲弓提出“居敬而行简,以临其民,不亦可乎?”是指内心能守敬,行事能简要不繁,能运用这一套方法以来面对天下黎民百姓,这不是很好吗?仲弓在孔子“可也,简”的基础上,分解成态度与实践两个面向,也就是说在“简德”之外,加了一个“敬德”,这样来面临天下苍生,才行得通。

第七篇 立大本,才能传道统
◎子曰:“述而不作,信而好古,窃比于我老彭。”
好一个“述”字,数典不忘祖。本章孔子强调遵循道统的传承,并且自谦述而不作。
华夏学问的内涵是从“人性”出发,以人性作信仰,走出人文的道统,《中庸》一开头讲得明明白白,“天命之谓性,率性之谓道”,中国人一贯传承的“道”,明明白白点出是从人性淬炼出来的,做人要坚持做合乎人性的事,不走违背人性的道路。天有好生之德、天无私覆地无私载,从效法天文、地文、自然文,走出“贵公”的王道。所以,《礼记·礼运篇》“大道之行也,天下为公。”从“性智”到“公天下”到“天下平”,这是道统的本末终始。孔子所强调“述而不作”的“述”,就是在坚持遵循这个道统的基础之上。
至于孔子所私自比拟于老彭,我们可以清楚地连接,老彭绝对是“述而不作,信而好古”的形象型前辈,这是“见贤思齐”。从大处的“本”说,“述”就是“述传统”,传统所传莫非“传承道统”,它和“政统”不同,政统时时在变,可是道统不二,立大本只有道统才是正统。
这个“述”最少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诠释:
第一,“述就是遵循人性之大用的道统”:天地之大德曰生,这个天有好生之德的天性,就是天德(含地德)好生。往上讲,最源头就是元德,“元者,善之长也”,就是说元德是一切始生之善,并且生生不已,没有尽头,这是元德。往人的世界讲,就是仁德,从仁者爱人到仁者无不爱也,这是“民,吾同胞;物,吾与也”,儒家这种民胞物与(民,吾同胞;物,吾与也)、恫瘝在抱的道统观,是遵循元德始生万物而不自恃其至爱的原性。《中庸》第一章:“天命之谓性,率性之谓道。”率性就是遵循人性之所发,发而皆中节,并且无所保留,这个“道”就是人性的大用,人性大用的极致,就是圣人的境界。
佛经《佛说十善业道经》第二十四集:“人生为己,天经地义;人不为己,天诛地灭。”所以,只要有为,人人皆可为尧、舜,人人皆可为圣人,它是以人性为本的道统观。天有天性、地有地性、金有金性、木有木性、水有水性、火有火性、土有土性、石有石性、草有草性……天地万物莫不有性,发挥物性的大用,这是天生物性最大的价值。于人而言,正是“天地之生最贵者也”,人人都有责任做好自我实现,理想的自我就是《中庸》第二十二章所说的先做好“尽己之性”,而后扩充做好“尽人之性”,然后做好“尽物之性”,这样最后才能做好“赞天地之化育”,才能做好“可以与天地参矣”的境界。这是“述”(遵循)人性之大用的道统观。
第二,“述就是遵循古圣先贤大居正大一统的道统”:从思想的建构而言,孔子在《书经·虞书》的《尧典》《舜典》标榜帝尧、帝舜、大禹一脉相承,选贤禅让;孔子《春秋》取鲁隐公以让心即位为《春秋》系年之始,这种“隐为桓立”的精神,也是“以公不以私”的让位情操。正所谓“大道之行也,天下为公”核心价值的具体作为。我们看看《礼记·礼运篇》的大同精神:
“大道之行也,天下为公,选贤与能,讲信修睦。故人不独亲其亲,不独子其子。使老有所终,壮有所用,幼有所长,鳏、寡、孤、独、废疾者,皆有所养。男有分,女有归。货,恶其弃于地也,不必藏于己;力,恶其不出于身也,不必为己。是故谋闭而不兴,盗窃乱贼而不作,故外户而不闭,是谓大同。”【评:《大同礼运篇》不是遥不可及的美好理想,而是基于生命之大本的行动指南。】
这是《春秋》从“大居正”思想,“政者正也”而止于至善的大同境界,讲到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而致太平的境域,这是“述”(遵循)中华文化“大一统”的道统观。
不作,就是遵循传承的道统,不妄自创作。《论语·述而第七19》子曰:“我非生而知之者。”孔子谦称自己不是“生而知之者”的上智之士,顶多就是学而知之者,这是希圣希贤的态度,他就是念兹在兹的好古敏求;同样在《述而篇》,他又说了一句相似的话,《论语·述而第七27》子曰:“盖有不知而作之者,我无是也。”不必去深究论辩孔子是“生而知之者”或“学而知之者”,这没有实质的意义!
我们要努力自我沉淀向孔子学习的,是他在《论语·述而第七19》说自己是“好古,敏以求之者也”;是他在《论语·述而第七27》说自己是“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,多见而识之。”如果圣人是自性而圣,贤人是自性而贤,孔子谦称自己无法像圣贤的自觉其性,自悟其性;《中庸》第二十一章:“自诚明,谓之性,自明诚,谓之教。诚则明矣,明则诚矣。”不能自诚而明,也要自明而诚,诚则明,明则诚,最后达到的境界是一样的。
《中庸》第二十章:“或生而知之,或学而知之,或困而知之,及其知之,一也。”这就是孔子“述而不作”的真功夫,是我辈学习追随的典范。【评:“立志”,前提是“立信”。信什么?信“圣人之心”人皆有之,在家天下的时代,这个话不敢公开说;如今,民智大开,可以鼓励大家都能回归生命的本源,不走宗教的路,不走商业主义的路。】

第八篇 天下是让出来的,而不是争出来的
◎子曰:“泰伯,其可谓至德也已矣!三以天下让,民无得而称焉。”
这一章的关键字是:让。
这一章是讲泰伯让位的佳话,泰伯的父亲是古公亶父(音胆府),周朝的先祖,后来周武王追尊为周太王。古公亶父生有三子,长子泰伯,次子仲雍(虞仲),三子季历(后来周武王追尊为王季),季历生子名叫昌,后来通称为西伯昌,即周文王(这还是周武王所追尊)。季历贤德,后来生西伯昌,天资聪颖,在众子中,古公亶父特别喜欢他。
按照家天下制度,周代以嫡长子作为帝制传承的依据。泰伯知道周太王欲立季历,以传其子昌。只有泰伯、仲雍两兄弟同时让出,才能真正完成让位,遂与大弟仲雍奔往荆蛮,于是周太王(古公亶父)乃立季历。让弟是让贤,这是了不起的举动。泰伯自号句吴,为春秋吴国的始祖。这是泰伯让位的至德,德必须有具体善行的结果,才叫作德,有至德故有至善,大人之德的最高境界就是止于至善。所以,太史公编撰《史记》将吴太伯让位列为《世家》第一。
同样地,伯夷是商纣王末期孤竹国君主的长子,弟仲冯、叔齐。伯夷是嫡长子,孤竹国君主临死前却指定叔齐为继承人,悖离传统嫡长子继承的宗法制度。叔齐不忍心与伯夷争夺君位,伯夷也不愿违背父亲的意志。后来伯夷和叔齐双双出走,听说西伯姬昌善待贤达老者,遂前去投靠,离开了孤竹国,王位就由大弟(中子)继任。西汉·司马迁将伯夷事迹列在《列传》第一篇,同样是表彰伯夷的让德。当然我们也不要忽略了“仲雍”“叔齐”的可贵。
《书经》是一部重要的典籍,《书经·虞书》先讲帝典——《尧典》《舜典》,尧禅让舜、舜禅让禹,标榜的价值无非就是让贤之德。从可以查考的信史开始,中华民族都是家天下的制度,天下都以“争”打来江山的,不是以“让”传承来的。所以,儒家《书经》这部经典首先提《尧典》《舜典》,这个“禅让”的思想自然是有针对性的。《论语·里仁第四13》子曰:“能以礼让为国乎?何有?不能以礼让为国,如礼何?”孔子这话说得很郑重,也说得很沉重。
“至德”这个词,在《论语》中出现过三次:
第一,《论语·泰伯第八01》子曰:“泰伯,其可谓至德也已矣!三以天下让,民无得而称焉。”这一章重点在讲“让德”。
第二,《论语·泰伯第八20》孔子曰:“……三分天下有其二,以服事殷。周之德,其可谓至德也已矣!”这一章重点在讲“仁德”。
第三,《论语·雍也第六28》子曰:“中庸之为德也,其至矣乎!民鲜久矣!”这一章重点在讲“人性”。
这一章是说泰伯有至高的德行,他的道德好到了极点。有治而无乱之德曰至德,有治而无乱之道曰至道,至道必从至德而来,有至德而后有至道,有至道而后有至善。所以,《中庸》第二十七章:“苟不至德,至道不凝焉”,至德是内圣之功,至道是外王之业。天无私覆,地无私载,这是天地好生的大德。法天法地法自然万象的大人,追求的无非是如天无不持载、如地无不覆帱的大德。《易经·乾卦·文言传》释九五:“夫大人者,与天地合其德”,与天地合就是“大人”的“至德”。有了最高的德行,才能成就最高的大道。就步骤而言,先修至高之德,才能凝结至高之道。《中庸》第二十七章:“大哉!圣人之道。洋洋乎!发育万物,峻极于天。……故曰:苟不至德,至道不凝焉。”“至德”“至道”,于人世而言,不就是“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”的道理吗?简单说就是一部《大学》的精华。
家天下的“大人世及以为礼”,无论是宦官之祸、外戚之祸、党锢之祸……纷乱大多是为了政治上的既得利益,而争而斗,而掠而夺,代代离不开这个铁则。结党营私、政权倾轧、天下流离失所,以致国失朝纲、社会动荡、民不聊生。这些都离不开争权夺势、利益纠葛等。两千五百多年过去了,家天下的政体瓦解了。可是人类并没有彻底解决人性的沉沦,人类并没有减少你争我夺、尔虞我诈的贪图。
“让”,在今天有价值吗?放眼当今世界,新的或旧的列强,鲜有道济古今的襟怀、鲜有国治天下平的担当。更多的是兼并天下以图自己国家的利益。合纵连横没有少过,拉帮结伙,用心所至,几乎都是国际上的阴谋算计。当中华民族如飞龙腾升之际,天下一家的文化思维,仍然十分时髦。“以鲁当新王”,期待“齐一变,至于鲁;鲁一变,至于道”。这种因其国而容天下的雅量,这种内其国而外诸夏——内诸夏而外夷狄——至乎夷狄进至于爵,远近小大若一的大一统思想,不正是调和当今天下的一剂良方吗?“让贤”与“包容”不正是人类走向和谐的康庄大道吗?让一让、融合融合,也是人类必须思考的大问题。【评:止于一,就是回到大生命的一体感,当然就有容乃大,当然就懂得礼让和退让。一个“让”字有大美!】

近期连载,未完待续……
– end –
相关视频推荐
《论语接着讲》
(读经典,需要有德行的老师引导着!)
▼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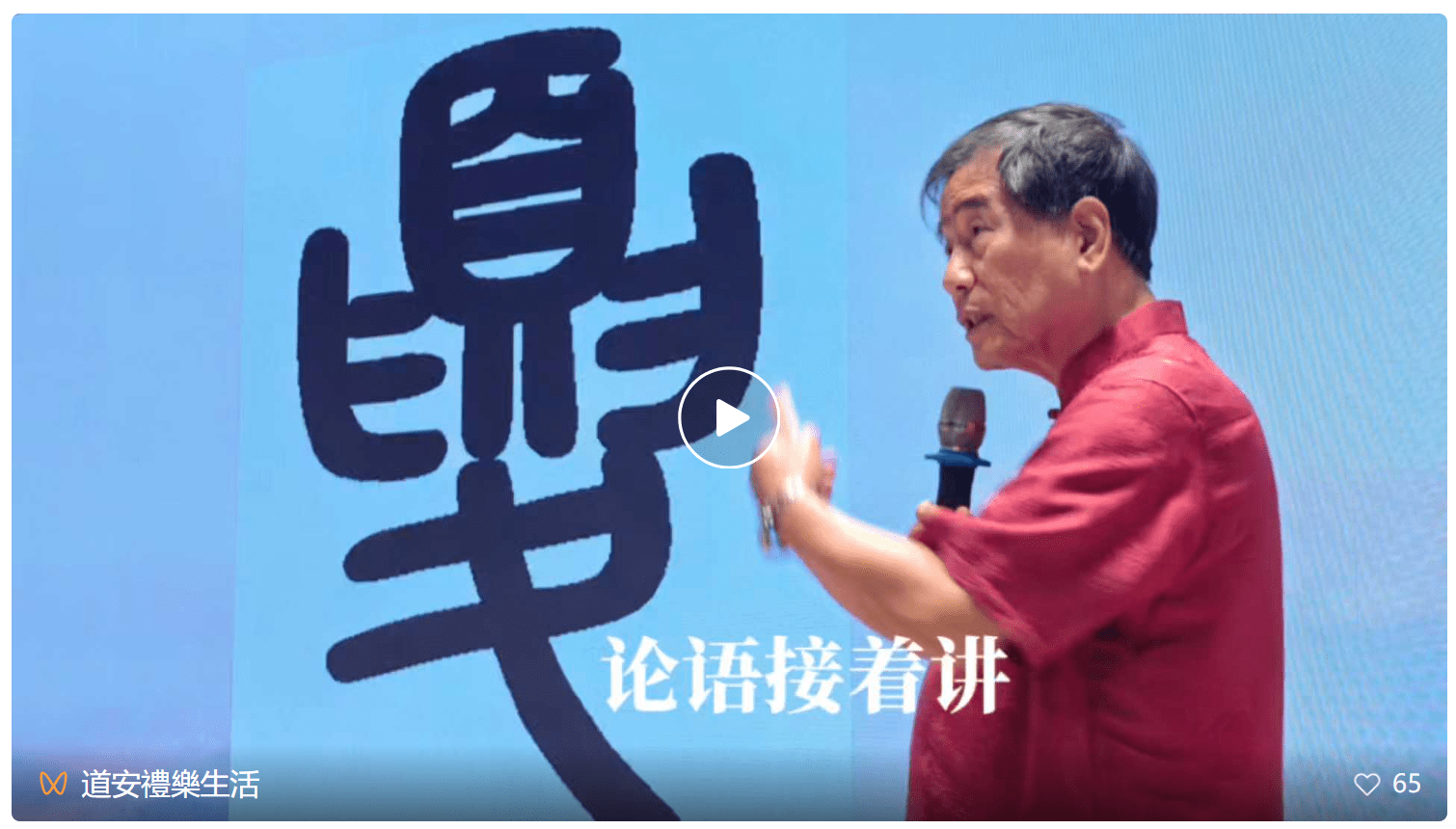
本文图片来自林明进老师。